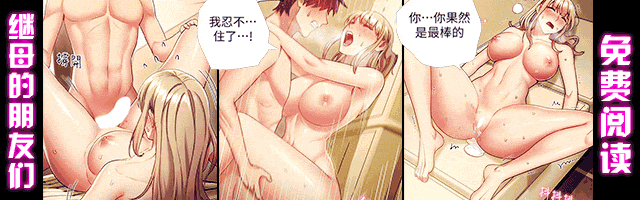是一团泛黄脱线的布制品。
真丑。丑得看不出样子。 但玄策知道,是个布老虎。
大概是玄策十二岁那年,守约被派去百越巡查。那种荒蛮之地,一般官员过去都是做做样子,守约却亲身下地,
和百姓同吃同住。南蛮多瘴气,守约回皇都后又强打精神陪玄策逛了一晚迎春夜市,护城河的寒风一吹,立刻就病倒了。
太医日日围在榻前,却不见好转,府里的下人急得团团转。一时难免有些言语带刺,暗指玄策是个灾星。
玄策好几次经过守约卧房,里面都是一群愁眉苦脸的老头,他便快步走开,去府外厮混,反正没人管他,能管的人病在榻上。
其实也不算厮混,并没有小孩乐意和玄策玩,玄策也看不上那些蠢物,他只是沿着守约带他走过的街道,再走一遍罢了。
他正低着头,踢石子玩,一位怪模怪样的老妇叫住了他。老妇穿着不似皇都人,一块破布摊在地上,摆了许多鲜艳的小玩意。
老妇说,这是百越镇邪压祟之物,摆在身边可保平安。
玄策觑了一眼,不过是哄小孩的玩意,嗤道:“这种东西要是有用,我早被镇死了。”
老妇又说,小公子家里是否有重病之人,如果诚心为病者做一个布老虎,能保他逢凶化吉。
鬼使神差般,玄策买了,躲在房里三天,缝了个灰容土貌的小家伙。
如果被看见他在守约旁边放东西,肯定会被仆从悄悄扔掉,于是他晚上溜进房间,轻手轻脚把丑东西藏在角落的褥子下面,飞也似地逃走了。
第二天,一直昏昏沉沉地守约居然醒了,病情也慢慢好转。
只是玄策再去偷偷寻那只布老虎,却如何找不到,他一直以为被哪个铺床的丫鬟拿走扔了。
“所以,哥哥,你到底知道多少……”玄策烦闷地把布老虎扔回木匣,转身离开了房间。
又一年,天下大旱,田地颗粒无收,民不聊生,民怨沸腾。然而这种危急时刻,户部竟拨不出什么银子;朝廷下令开仓放粮救济灾民,各地官员却支支吾吾,互相推辞,就是拿不出半斗谷。
明眼人都知道朝廷已如被白蚁蛀空的朽木,岌岌可危,离倒塌只有一步之遥。
守约比以往更加忙碌,常常大半个月才回一次宫。
他的面容疲倦而平静,只道气数已尽,顺势而为。
三月后,定王百里玄策举兵造反,一呼百应,四方将领同时叛变,拥他为王,大军集结直逼皇都。
都城人人自危,不少人提前南下避难。慌乱之际并没人注意,平远伯全府已然失踪。
平日只炼丹求长生的皇上慌了心神,多次传召守约入宫,逼他拿出对策;皇后日日在后宫咒骂当初不该养一头白眼狼。
一日傍晚,天色阴沉。管事突然把我和我的侍女们带上停在后门的马车,马车后是一列沉默的货队。我立刻明白守约要把我送走,掀开帘子望向宫门。
难得的雨倏忽而下。
守约笼着袖子,背靠朱红描金的小门,管事撑起油伞。雨淅淅沥沥顺着屋檐汇成细小的水柱流下,从伞面迸溅向上空。
他抬头看着青灰色的天,眼神清亮,带了一丝笑意。
像是漫长的等待有了结果。
定王大军兵临都城那天,守约作为主帅登上城楼。
一里外,张扬红发的主人握住黑骑的缰绳,耀武扬威似的出列,驶向城墙。
他仰头扫视了一圈严阵以待的士兵,弯了弯唇角,嚣狂自信的眼神钉在守约身上,毫不掩饰暴戾和欲望。
守约身旁的士兵捏紧弓弩,随时都能射杀这个战乱之源。
“别动他。”守约语气淡然却肃杀,“他是我弟弟,别让我背上屠戮手足的罪名。”
这场战斗以定王暂退告终。皇都本就易守难攻,而且守备充足,相对定王军长期跋涉,粮草不足,两方一时竟僵持不下。
谁知到了半夜,城西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,紧接着居民躁动起来,哭喊声此起彼伏。
“快跑啊,护城河的水漫进来了!”
“救救我,救救我!”
护城河被恶意炸开,城西作为全都地势最低洼的地方首当其冲。那些小水渠常年堵塞,居民多次上报朝廷,无人处理,完全失去疏通作用。大水一下冲垮了水渠连同绝大部分建筑,叛军趁乱攻入,在城中肆意纵火。
躲在家中收拾金银细软的高官们吓破了胆,挺着肥胖的肚子赶到东宫求助太子,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!东宫的仆从、侍卫、门客等早早地被遣散,各自逃命去了。
高官惶惶然破口大骂,忽然一道银光闪过,鲜血迸溅,脏话卡在喉咙没了生息,脑袋骨碌碌滚到地上。
百里玄策纵马冲入东宫,手起刀落解决了几个吵闹的蛆虫。他看到遍地狼藉,脑内警铃大作,胸口好似坠了一块巨石往下沉,立马燃起暴烈的怒火,冲向内殿。
一路搜查,最后他闯入景苑,只见房梁上挂着一匹白绫,下方摆着一方木凳。
魂牵梦绕的人正站在木凳上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百里玄策瞬间止了呼吸。
“百里守约!你敢死试试!”
他一剑斩断白绫,将人
掳上马,向皇宫飞驰而去。
守约被暴力扔在榻上,床发出一声轻响。这是一座很不打眼的小殿,十分陈旧,某些难以打扫的地方甚至积了一层污垢。
玄策坐在榻侧,一边撩开守约的衣襟,抚摸他胸前的乳粒,感受敏感的乳粒在他手下充血发硬,一边说:“哥哥,我就是在这里长大,今天我要在这里肏你……”
守约乱了呼吸,却没有说话,或许觉得事到如今语言已经太苍白,只有一场性事能让两方都痛快发泄。他静静地打量这间屋子,任由衣服被扯得凌乱不堪。
玄策突然恨极了这幅模样,自己走的每一步都好像在某人的计算内。令他不快的人应该卑贱到泥土里,而不该躺着享受。
他松开手上红樱,冷冷地说:“把人都带上来。”
“你这个畜生!你这个乱臣贼子!”皇后被绑住,跪坐在地上,身旁是已经晕过去的老皇帝和一众瑟缩的太监宫女。他们拥着老皇帝逃出宫,却被玄策的人捉住,绑起送回了宫。
“你不得好死,你这个毫无廉耻的东西!”皇后一边哭一边骂,“他是你皇兄啊!”
回应她的只有帐内赤裸交错的人影和一声高过一声的呻吟,似痛苦,又饱含欢愉。
“玄策……啊……出去……让她们出去……”
守约把头埋进床褥里,想要咬紧床被,口腔却被强硬地塞进三根手指,逸出挡也挡不出的喘息。
“你的好儿子可被我干得爽哭了,射了我一手呢。”百里玄策狂妄地笑起来,身下冲撞得愈发猛烈,顺势扬起沾满白浊的手。
“真淫乱,天生就适合挨肏。”
皇后气得疯狂咒骂,却劈了嗓子,只能双目圆睁,嗬嗬长嘶,被迫听床上一声声淫词浪语。
玄策骑在守约身上,按住守约的薄腰,从背后狠狠贯穿。
“看看你教养的好儿子,正在和弟弟乱伦呢,紧得要把我夹射了……”
他的冲撞丝毫不讲章法,只管挺入粘湿的穴道,撞击脆弱的肉壁,然后不顾媚肉层层吮吸挽留,全部拔出,再次狠厉地撞入。
泪水模糊了守约的视线,床剧烈的摇动、皇后尖利的咒骂和自己的哭喘好像远在天边,他全部精力都在应付体内巨大霸道的性器,和一波一波的快感。
他感觉自己要被浪潮淹死了,背上的结实的重量压得他呼吸困难。他只知道自己被肏射了,身体内部还在不停的被捅开,太深了,顶得他十分难受。他屈起手指抓住被褥,想要往前爬,摆脱体内巨物的捅弄,然而他稍一用力,就被身上仿佛要把他嵌进身体的力量压下,只能顺从本能地喊叫。
“我要死了……放开我……啊……”
玄策如愿以偿地放开他,把他翻转过来。胸腔不再被挤压,守约挺起胸大口大口呼吸,稍微在情欲浪潮里恢复了一丝清明,然后被再次凶狠地插入。
“哥哥你怎么敢死。”玄策掐住他的脖子,泄愤似的看身下人急促地呼吸,挣扎无力地去掰他的手,身下肉洞又紧又密,每一次紧致收缩都像在敲击他的骨髓,“你要是死了,就没人管得住我了。都说我是最像皇帝老头的人,我每天都杀个人来玩,说不定也要和弟媳通奸。不过我有那么多哥哥,看上兄嫂的可能性更大。”
“哥哥,我去和大嫂通奸好不好,生下的孩子不知道是你的还是我的,我都封做小太子。”
玄策松开手,恶意地盯着眼前溺于情欲的脸,伏在守约胸前噬咬虐待两个艳红的小肉粒,把完美如白玉的身体弄得青青紫紫。
“我从前有多爱你,现在就有多痛恨你。”玄策狞笑,“你这个虚伪恶心肮脏的骗子。”
“啊……你住口……别说了……求求你……”
“怎么,不想让别人给我生孩子?”玄策握住守约的手,引他抚摸肚子上被性器顶出的凸起。近年来守约瘦的厉害,性器的形状分外明显。
守约仿佛被吓到,触电般想缩回手,却捉住被强制按在腹部。
“哥哥,那你给我生啊。”玄策恶劣地咬他耳朵,“到时候你挺着大肚子挨肏,怀一个生一个,生一个怀一个,永远都躺在床上。”
“你摸摸看,肚子里的孩子在动。”
“不可能……你骗我……”守约激烈地推拒他,“这里怎么可能有孩子……”
玄策爱极了他在床上被肏得晕乎乎后什么都信的幼儿模样,又痛恨他的背叛,再次加大身下的讨伐力度,把守约刺激得晕过去。
第二天传来消息,皇上薨逝,定王登基,杀了宫内几乎所有的太监宫女给先皇陪葬,并且将皇太后送至远郊古寺修行。
据传,送出宫的皇太后疯疯癫癫,满口胡言乱语,不知她被做了什么。
更惊世骇俗的是,定王登基后第一件事,便是封先太子为皇后。有异议者拖出去先打五十大板,打完仍不服者,斩首示众。
新朝几乎砍掉了旧朝一半官吏的脖子,没收贪官污吏全部家业,重新选拔人才,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百姓民
生的法令。终于让日暮西沉的国家重焕生机,步入正轨,缓缓运作起来。
巍峨的宫殿里,文书叠了满地,夕阳拖曳出长长的影子,是个清瘦男子模样。
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靠近,搅乱了原本安静的影子。
百里玄策从背后搂住守约,下巴靠在肩膀上,双手不安分地挑开衣襟,他向守约耳朵吹气。
“哥哥,我刚刚见了吕家的长女,就是你的太子妃——”他故意拖长了尾音,一听就是要闹事,“她对你真上心,不但对这几年细细解释,让我放心,还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。”
“生怕我把你弄死……”
守约被他撩拨得乱了呼吸,只好先丢了笔,按住在他身上作乱的手。
“你能心平气和地见她了?”
“我想她死啊。每个让我难过的人都得死,我嫉妒她嫉妒了四年,夜夜都想割了她的喉咙。”玄策语气突然变得柔和,讨好似的亲吻守约的脖颈,“但是哥哥你不让嘛,我就不能杀。”
守约侧身勾住他的脖子,一遍一遍轻轻啄吻他的唇。
那还真委屈死你了。